2003年非典后来为什么消失了?关于非典,我那些模糊和清晰的记忆
我已经记不太清楚,我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“非典”这个词的。
关于这个词,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段子,说典韦救了曹操的命,然后曹操感叹了一句:“非典,吾命休矣。”
明知是段子,依然乐于传播。2002年前后,网络刚刚在中国流行开不久,那时候传播这些段子的主力军,除了QQ,还是短信——发一条一毛钱的短信。
我当时在重庆,距离最先爆发出非典的广东很远,心里其实并不太害怕。
真正让我开始意识到害怕的,是一件关于足球的事情。
2003年2月份,新科世界冠军巴西队来广州跟中国男足踢了一场比赛,比分是0:0,球迷们欢欣鼓舞,但是我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说法,说巴西队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踢球的,而且他们很多队员在公共场合都戴了口罩。
这件事,让我们开始意识到,这次的疫情有点严重。
然后,我又意识到,我们重庆有很多人在广东打工,春节,他们都回家了。

没过多久,我就去了重庆青年报工作,在旗下的《激动周刊》当了一个见习记者兼见习编辑。
时间很仓促,我来不及租房子。正好我以前在药厂上班的同事家就在报社附近,就给我腾了一间屋子,让我暂时住着,边上班边找房。
周刊记者不需要每天上夜班,更多的是深度报道和策划报道,所以不需要每天去报社开选题会。但是即便是这样,我们也能从新闻部门的记者口中了解到,重庆也开始出现了患者。
而且患者出现的区域,距离我们生活的地方,越来越近。
大家心中都有点惶恐,报社已经开始有人戴着口罩上班。
那时候似乎流传着“醋能杀菌”的传说,办公室里经常弥漫着一股醋味,跟烟味混在一起,说不出来的让人觉得心慌。
那时候好像也在宣传,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,要打开窗户通风。
采访的时候出门挤公交,几乎每次都能遇到乘客为了开窗还是不开窗争吵,一边是怕冷,一边是怕病,谁都不让谁。

我还是没戴口罩,一方面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,另一方面,我近视。
近视和不戴口罩的关联,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明白。近视就要戴眼镜,戴了口罩之后,鼻梁旁边的口罩缝隙哈出来的热气就要在眼镜上起雾,什么都看不清。
让我改变主意的,是一个电话。
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,我当时正在湖广会馆采访,接到了我们周刊卢副主任的电话。他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跟我说:“报社死了一个同事,你现在不管在干什么,马上来报社,可能要隔离。”
那年我还不满27岁,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砸到我的头上。
更关键的问题的,2003年的湖广会馆,残破而杂乱,人潮拥挤,远不像现在这般光鲜亮丽。
我看着身边川流不息的人群,有的在吐痰,有的在咳嗽,有的在大声说话唾沫飞扬,我感觉周围就像是一幅静止的画,画上的每一处都涌动着非典的病毒。
我给卢主任说:“我正在采访,怎么办?”
卢主任像一个指挥官一样回复我:“不采访了,回来。”

从渝中区解放碑回江北区大庆村的这段路程,可能是我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段路。
在公交车上,我先给我家里打了一个电话,告诉他们报社死了一个同事,我们可能要隔离,近期我不能回家了。
他们在电话里很着急,我只能安慰他们,说没什么大事,常规消毒而已,放心。
话是这么说,其实我心里比他们还要紧张。我虽然刚刚入行,但是我也知道,报社的记者要出入所有可能接触到感染者的场所,真要是出了问题,我们每个人都得经历一次严格的检查。
而且还不知道检查结果如何。
然后我给收留我的药厂同事打电话,告诉他我收到的情况,跟他说,我今天晚上不一定能回来住,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。我房间暂时不要进去,如果一旦确诊,请他在自己工作的药厂带回来消毒设备进行消毒。
我同事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,跟我说,没问题,他晚上下班的时候会带一盒最好的口罩回来,如果我回家住,就分我一半。
我严格遵守了领导的规定,哪里都没去,直接回到了报社,觉得心情悲壮得不得了。
到了办公室之后,整个部门面面相觑,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,也不知道我们会接受怎么样的隔离。
还有敬业的记者在问:“要是我们都被隔离了,我们报纸还出不出?”
这样惶恐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,很快,周刊的李主任就来到我们中间,告诉我们,去世的那位同事,并不是因为非典,而是因为通宵打游戏,太疲倦,在进入报社大门的时候摔倒在地上,心脏病发作去世的。
一时间,大家的心情……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措词,因为确确实实有点对逝者不敬。

真的是觉得虚惊一场,甚至有点劫后余生的喜悦感。
大家各自拿起电话,把今天打过的电话又打了一边,告诉了最新的进展,然后重新联系接下来的采访。
我药厂的同事跟我说:“口罩我还是给你带回来,小心驶得万年船。”
当天晚上我想了很多,我这个同事是一家三口,孩子还没上小学。
我作为一个记者,每天东跑西跑的不知道要接触什么人什么东西,留在家里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。
第二天,我戴上了口罩,买了一张80厘米宽的折叠行军床,搬到了我们报社同事的合租房里。
两室一厅,我当厅长。
三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凌晨写完稿子,到楼下吃一碗鳝鱼面,喝两瓶老山城,然后回去睡觉,直到不久以后其中一位同事辞职去了新京报,我才结束了自己厅长生涯。
至于那一场非典,究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,我已经毫无记忆,记忆最深的,就是那一次半途而废的采访,以及当时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。
提供给我暂住的老同事,去了外省,现在不知道在哪里,很多年都联系不上了。
以前在青年报一起工作的同事,也分散到各个报社,现在又分散到各个行业,很多都联系不上了。
那时候的人,有时候会想起聚一聚。
但那时候的日子,真的再也不想尝试了……
(责任编辑:admin)


 广东一制毒窝点发现542枚
广东一制毒窝点发现542枚 央媒评西安地铁保安拖拽女
央媒评西安地铁保安拖拽女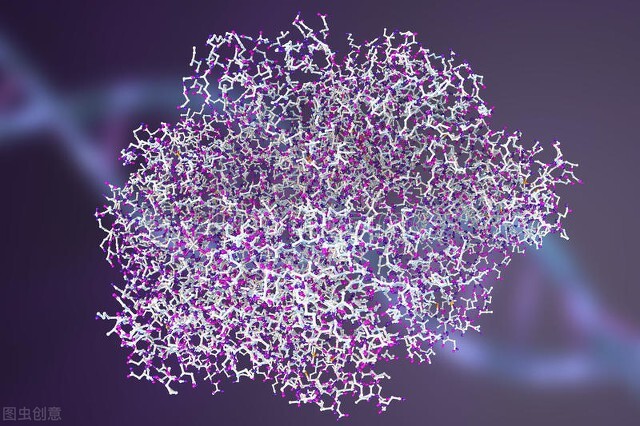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!全国已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!全国已 五千多的鞋子,穿一会就开
五千多的鞋子,穿一会就开 华为回应孟晚舟引渡案结束
华为回应孟晚舟引渡案结束 悲剧!廉江4个小
悲剧!廉江4个小 15岁初中生弑母
15岁初中生弑母